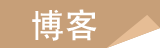
香港立法會選舉將在12月7日舉行,筆者呼籲合資格選民積極投票,選賢與能,優中選優。
筆者在大學時代適逢中英就香港回歸達成共識,當時不少人都期望「香港民主回歸」。筆者也積極參與其中,並有幸透過當時全香港大專學界同學們一人一票選出成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學界代表。筆者當年積極參與《基本法》有關九七回歸後的特區政制討論,並熱切期待香港回歸。在香港鐵定於1997年回歸的大背景下,自1841年開始強行佔領香港的英國殖民地者也在1980年代也逐步「開放」政制。大家必須注意的是:英國殖民地者竊據香港逾百年,但都一直沒有開放政制。最具象徵意義便是當時的立法機關(立法局)主席一直由英國女王委派的總督出任。即是說行政立法權力都掌握在總督手中。1843年立法局成立,香港總督一直是其主席,直到150年後的1993年,即距離回歸還不到4年才改由港英信得過的議員出任主席。
曾任港督超過10年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 1947-1957年在任)便在其回憶錄《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中說:「在英王的殖民地上,總督權力僅次於上帝」(In a crown colony, the Governor is next to the Almighty)。葛量洪的坦言,足證當時港督權力之大。可以說,在155年的香港被佔領史中,英國殖民地者一直都沒有開放政制。一直到了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英國殖民地者才急急忙忙開放香港政制,容許極其有限的政治參與。最具象徵意義的便是1985年9月才有首次香港立法機關選舉,當時還沒有直接選舉。香港立法機關首次的直接選舉要等到1991年;那時距離香港回歸還不到6年時間。英國殖民地者對香港的專制統治,彰彰明甚。
另一具象徵意義的是當時香港立法機關內有官守議員。官守議員完全退出香港立法機關要遲到1995年。近日獲美國駐港總領事伊珠麗「垂青」的陳方安生,她便是港英精心培養的高等華人之一。陳方安生在1993年開始出任布政司,相當於今天的政務司司長,是香港排名第二位的行政首腦。陳方安生在1995年前便以布政司身份成為香港立法機關成員,有份投票;即在立法機關內有票去為行政機關提出的政策護航。這和今天特區的行政機關, 在立法會內「一票都冇」,不可同日而語。兩相比較,大家便明白誰真正啟動了香港民主化的步伐,是我們祖國。因為中央提出「港人治港」,且嚴格遵守。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內沒有京人,只有港人。中央甚至容許外國法官坐陣香港各級法院。香港和紐約、倫敦齊名,合稱「紐倫港」,以顯示香港作為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你能想像紐約和倫敦會有外國法官坐陣其各級法院,包括其終審法院嗎?
相對葛量洪口中的「僅次於上帝」的港督權力;回歸後的特首,權力遠不如港英時代的總督。特首和他的團隊在立法會內沒有票,特首不是立法會主席,不能控制立法會議程。特首不能委任社會賢達出任立法會非官守議員,以便穩住在立法會內的票數。由於中央恪守「港人治港」的政治承諾,特首必須是香港人,不能是京人或內地其他地方的同胞,且由香港本地選舉產生。這和港英年代,香港人連誰會當下任港督,都無從置喙。近年便有英國公開的檔案披露,1992年的英國首相馬卓安便曾考慮過把英國查爾斯王子即今天的英國國王,委派為香港末代港督;只是後來基於種種原因,馬卓安選擇了剛在選舉中失利的好朋友——彭定康而已。
簡單回顧港英年代歴史,是想告訴港人尤其黃絲,不要神化港英年代。黃絲眷戀回歸前,實情是當時港英統治是極其高壓的統治,和民主沾不上邊。港英殖民地者只是因為要把香港交還了,才心不甘情不願地「開放」政制。正本清源,認清歷史,有助我們更明白今天局面,應感恩誰,應譴責誰﹗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投票已截止,多謝支持